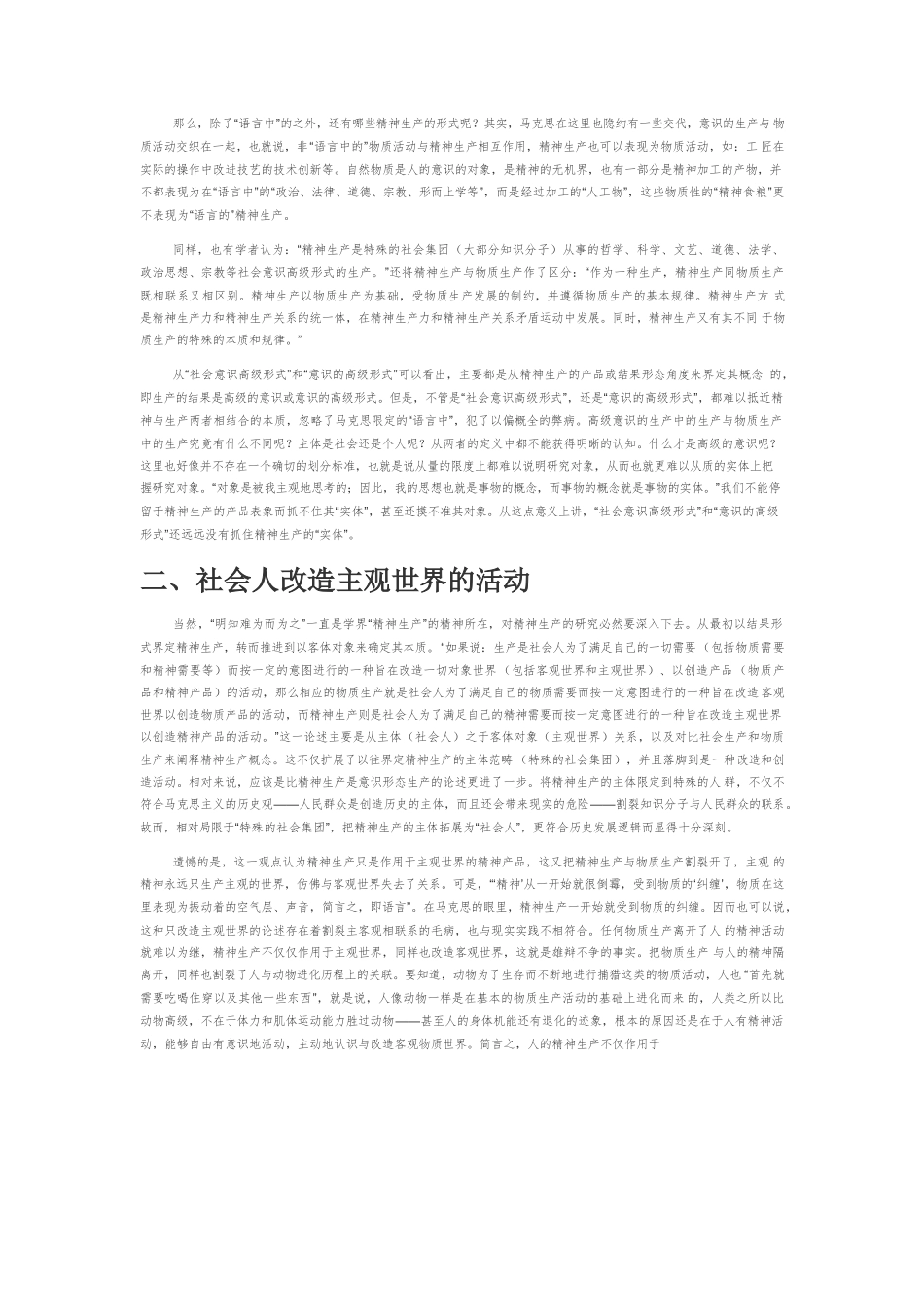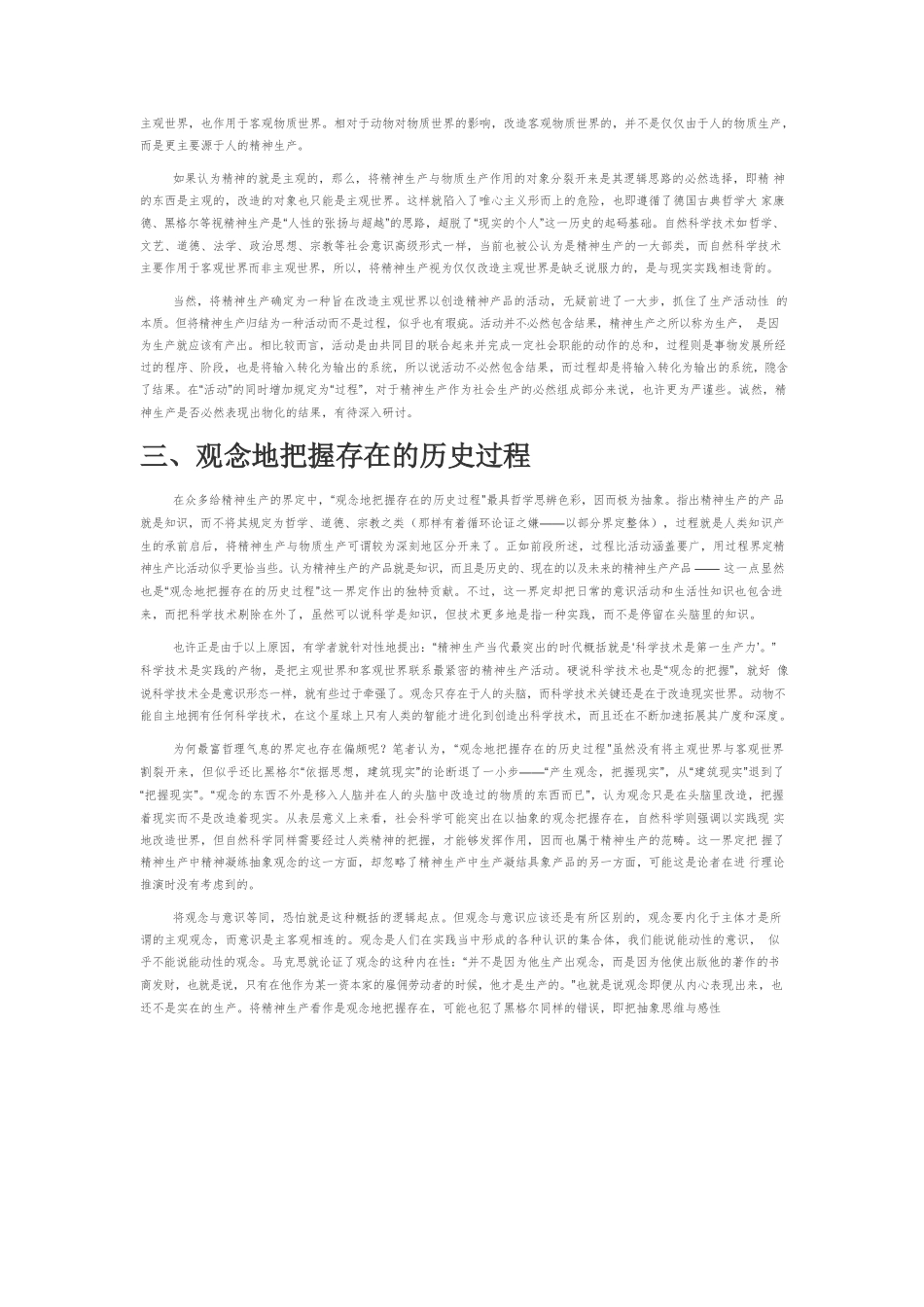【党课讲稿】马克思精神生产的创新实质提要:精神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学界对其界定至今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意识的高级形式生产或社会意识高级形式的生产,也有的主张是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还有的断定是观念地把握世界的过程,但都几乎认为创造或创新是精神生产最基本特征或实质,只是又在概念界定中予以忽略。要把创新真正确定为精神生产的实质,就需要去除三层观念障碍,从而使其更具有现实的理论价值。既能以创新区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辨别文化艺术品的简单重复制作并不是真正的精神生产,又能使往往陷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创新思想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渊源,还能♘揭示创新真正来源于人的本质力量。当今时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但在哲学上究竟怎样定义创新,至今还处于一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争议阶段。我们不妨回到马克思,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渊源。精神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说明马克思精神生产与创新有颇多相通之处:前者可以抒发诗情“上九天揽月”,后者亦可以创造器物“下深海捉鳖”;前者可以宏论宇宙之广袤,后者同样可以细探原子之微小;前者可谓瞬息万变穿越古今,扶摇直上九万里,后者则为科技生翼,实现“远程在场”和“速度恐怖”。换言之,精神生产属意精神的始源,在意生产的形式,创新则注重生产的结果,看重精神的实效;精神生产离不开精神的“起舞”,创新更依赖精神的“拓荒”。既如此,两者到底存在何种关联,是值得细究深思的。在经典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精神生产进行明确的界定,只是在论述物质生产时,有几处行文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了精神生产,最典型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为“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这是以生产的结果形式进行的表述,还不是对精神生产作出的概念论断。所以,要理清创新与精神生产的关系,首先需要确定马克思精神生产的概念。学界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的界定有几类不同观点,但都有一定的偏颇,故笔者将择其要点进行论述,逐层剥开遮掩在精神生产研究上的观念障碍,探寻其创新实质——这一共同识见,以资方家论伐。一、意识的高级形式或社会意识高级形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称之为精神生产。他同时提到,“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可能正是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把精神生产与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论述,以致学界最初就把精神生产认定为意识形态的生产。有学者就认为:“意识的高级形式——哲学、道德、宗教……等的生产,即‘精神生产’”。将意识反映与精神生产区分开,这是极为有意义的努力。毕竟日常意识太过稀松平常,与高贵灵动的精神还是应有所区别的,如果把日常意识也纳入精神生产,就把精神生产理论庸俗化了。这不仅不符合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早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人探讨精神生产的出发点,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研究精神生产的本意,他们的目的最初都是出于考察社会财富的增长而着手精神生产理论阐发的,只不过德国古典哲学侧重于人之本体性生成与超越,从理论导向理论,而马克思着眼于“理论的武器”和资本的增生,从理论导向现实。但是,在研究精神生产理论时,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语言中的”这一精神生产的限定语,也即马克思只是把“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看作是语言中的精神生产,而不是精神生产的全部,因为“语言中的”与“语言的”这两个限定词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示除了“语言中的”之外,还有非语言表示的类型存在;后者则限定精神生产完全就表现为语言式的,没有其他类型。因此,将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解为“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这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