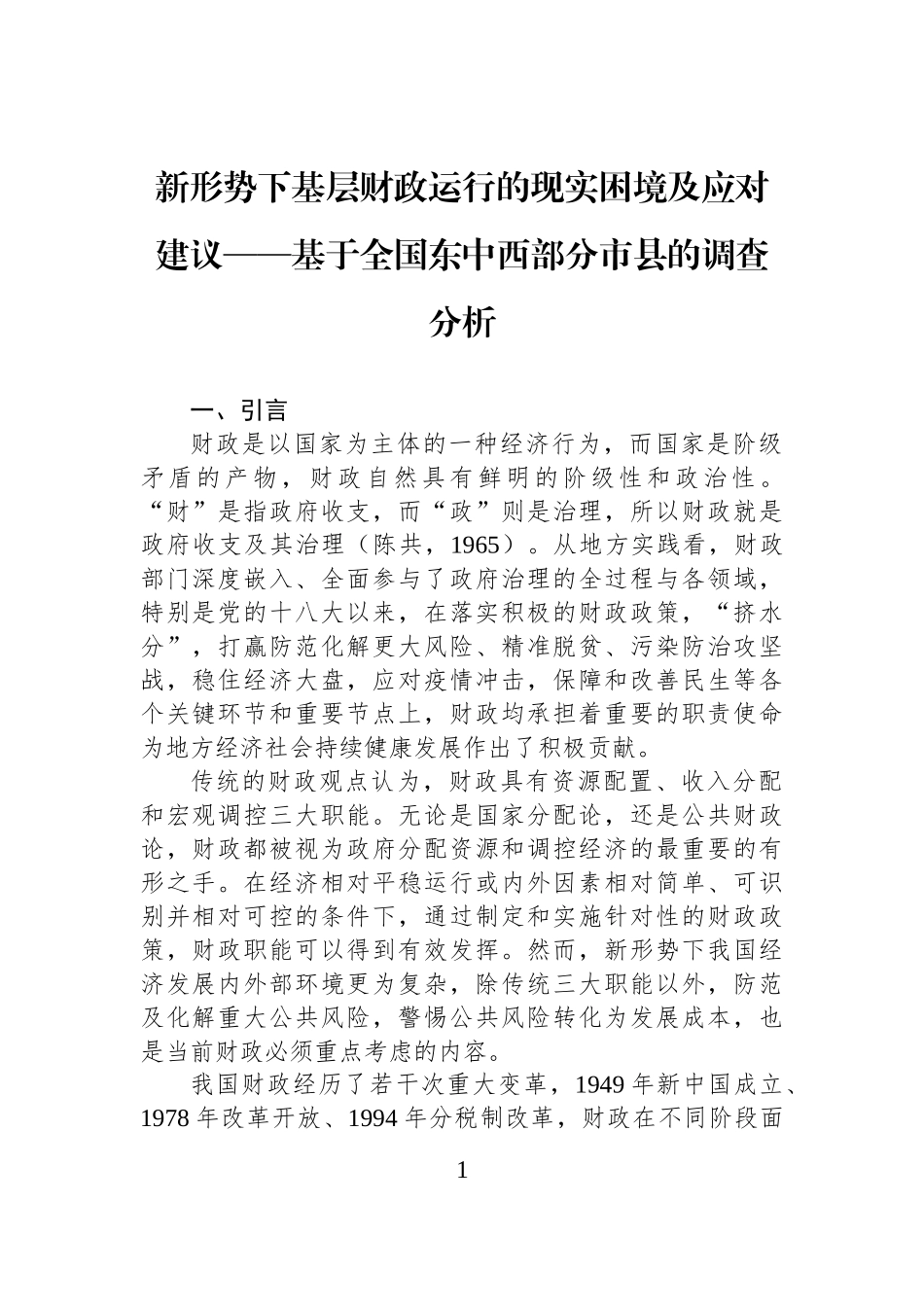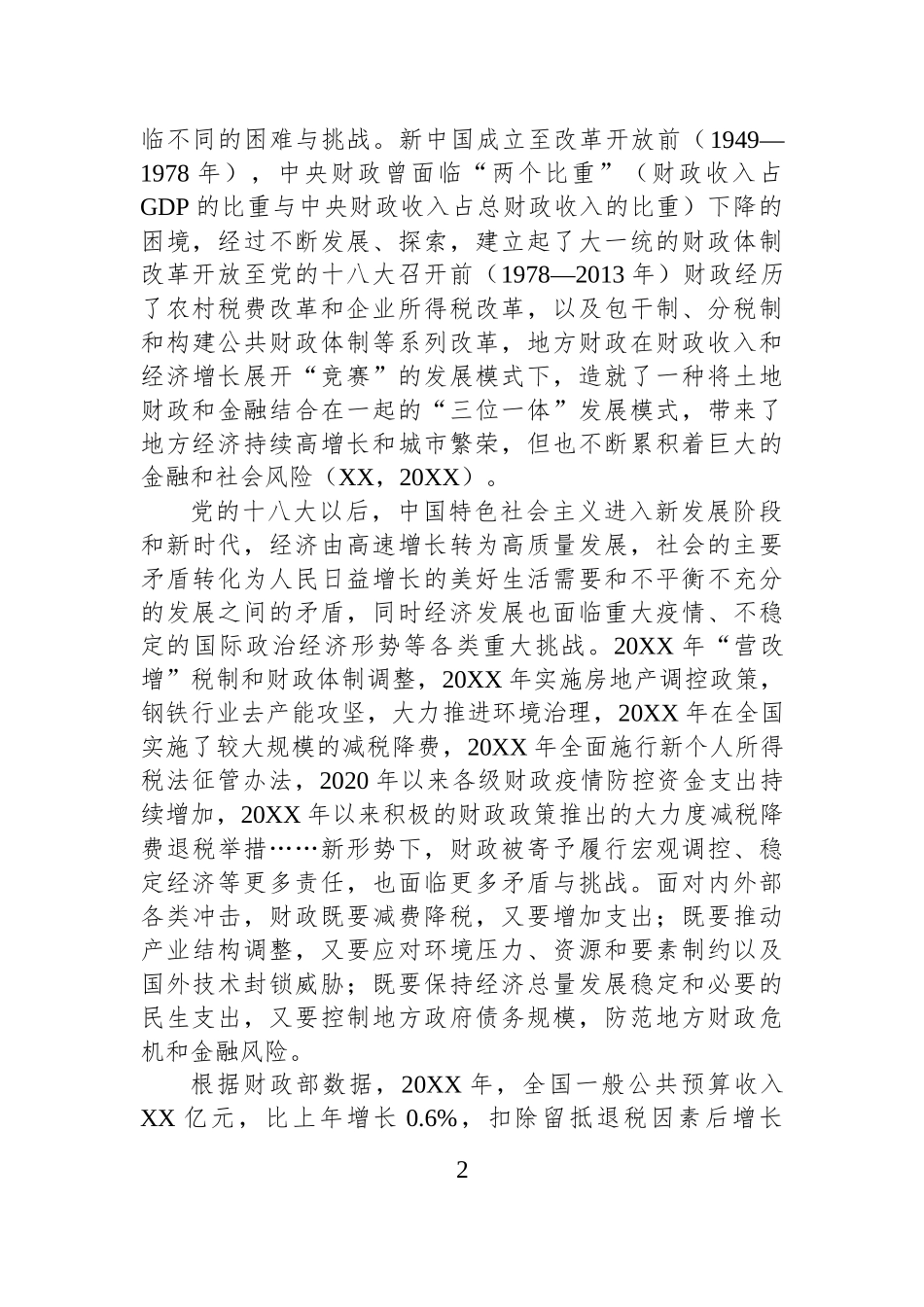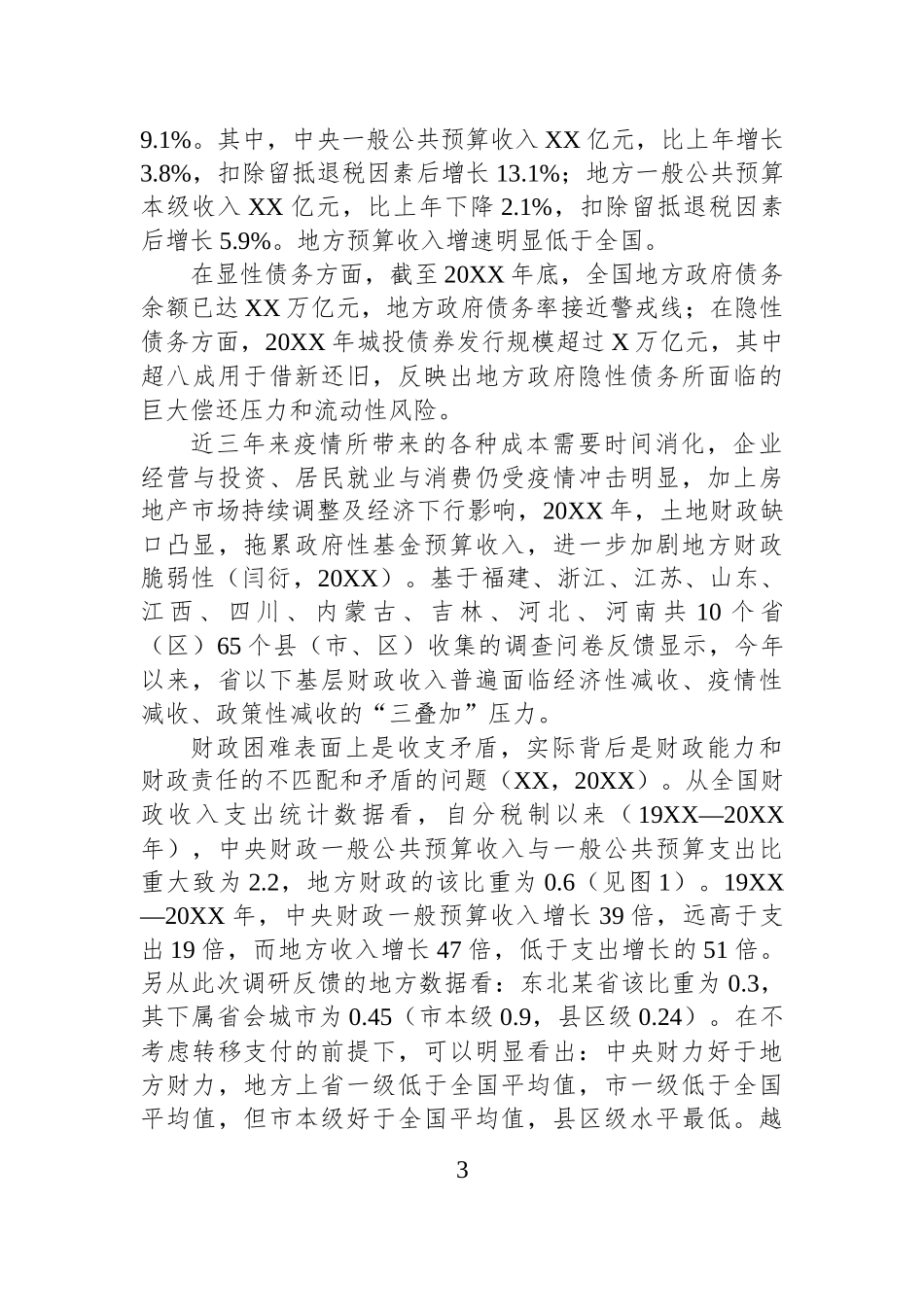新形势下基层财政运行的现实困境及应对建议——基于全国东中西部分市县的调查分析一、引言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一种经济行为,而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财政自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财”是指政府收支,而“政”则是治理,所以财政就是政府收支及其治理(陈共,1965)。从地方实践看,财政部门深度嵌入、全面参与了政府治理的全过程与各领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挤水分”,打赢防范化解更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稳住经济大盘,应对疫情冲击,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各个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上,财政均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使命为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传统的财政观点认为,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三大职能。无论是国家分配论,还是公共财政论,财政都被视为政府分配资源和调控经济的最重要的有形之手。在经济相对平稳运行或内外因素相对简单、可识别并相对可控的条件下,通过制定和实施针对性的财政政策,财政职能可以得到有效发挥。然而,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更为复杂,除传统三大职能以外,防范及化解重大公共风险,警惕公共风险转化为发展成本,也是当前财政必须重点考虑的内容。我国财政经历了若干次重大变革,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1994年分税制改革,财政在不同阶段面1临不同的困难与挑战。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中央财政曾面临“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的困境,经过不断发展、探索,建立起了大一统的财政体制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1978—2013年)财政经历了农村税费改革和企业所得税改革,以及包干制、分税制和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等系列改革,地方财政在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展开“竞赛”的发展模式下,造就了一种将土地财政和金融结合在一起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带来了地方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城市繁荣,但也不断累积着巨大的金融和社会风险(XX,20XX)。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和新时代,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经济发展也面临重大疫情、不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各类重大挑战。20XX年“营改增”税制和财政体制调整,20XX年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钢铁行业去产能攻坚,大力推进环境治理,20XX年在全国实施了较大规模的减税降费,20XX年全面施行新个人所得税法征管办法,2020年以来各级财政疫情防控资金支出持续增加,20XX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出的大力度减税降费退税举措……新形势下,财政被寄予履行宏观调控、稳定经济等更多责任,也面临更多矛盾与挑战。面对内外部各类冲击,财政既要减费降税,又要增加支出;既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又要应对环境压力、资源和要素制约以及国外技术封锁威胁;既要保持经济总量发展稳定和必要的民生支出,又要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防范地方财政危机和金融风险。根据财政部数据,20XX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XX亿元,比上年增长0.6%,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29.1%。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XX亿元,比上年增长3.8%,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13.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XX亿元,比上年下降2.1%,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5.9%。地方预算收入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在显性债务方面,截至20XX年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达XX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接近警戎线;在隐性债务方面,20XX年城投债券发行规模超过X万亿元,其中超八成用于借新还旧,反映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所面临的巨大偿还压力和流动性风险。近三年来疫情所带来的各种成本需要时间消化,企业经营与投资、居民就业与消费仍受疫情冲击明显,加上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及经济下行影响,20XX年,土地财政缺口凸显,拖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进一步加剧地方财政脆弱性(闫衍,20XX)。基于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江西、四川、内蒙古、吉林、河北、河南共10个省(区)65个县(市、区)收集的调查问卷反馈显示,今年以来,省以下基层财政收入普遍面临经济性减收、疫情性减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