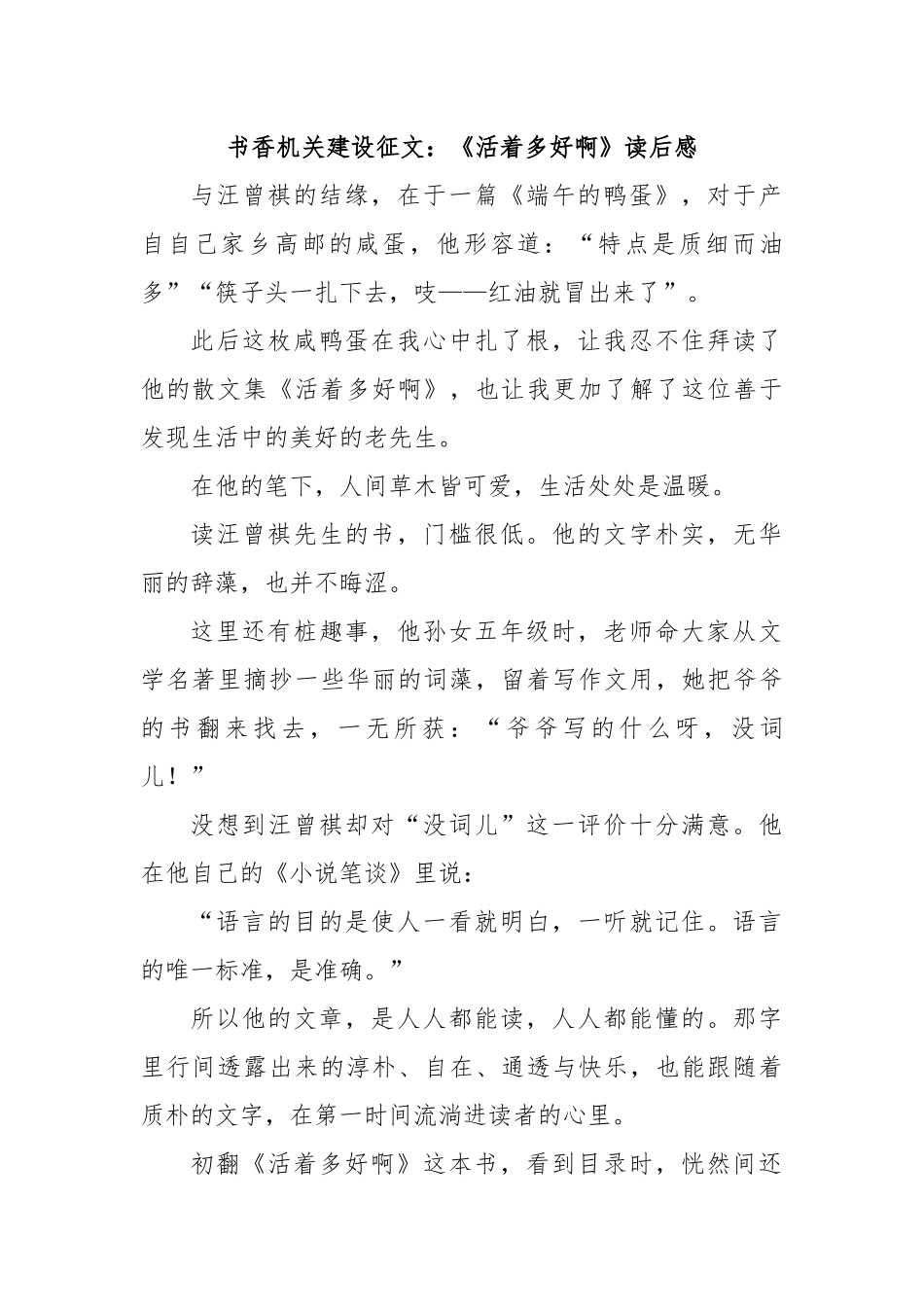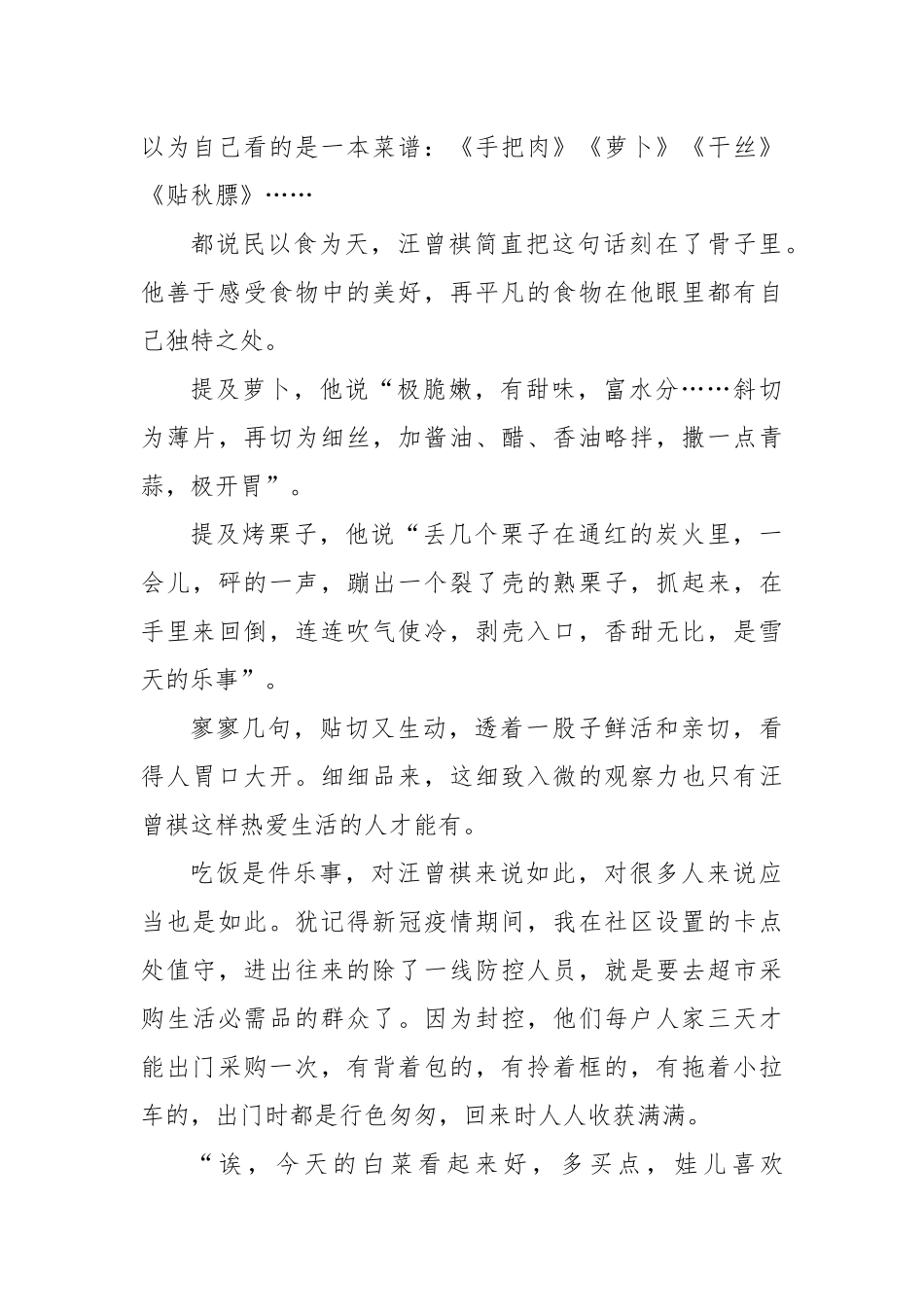书香机关建设征文:《活着多好啊》读后感与汪曾祺的结缘,在于一篇《端午的鸭蛋》,对于产自自己家乡高邮的咸蛋,他形容道:“特点是质细而油多”“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此后这枚咸鸭蛋在我心中扎了根,让我忍不住拜读了他的散文集《活着多好啊》,也让我更加了解了这位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的老先生。在他的笔下,人间草木皆可爱,生活处处是温暖。读汪曾祺先生的书,门槛很低。他的文字朴实,无华丽的辞藻,也并不晦涩。这里还有桩趣事,他孙女五年级时,老师命大家从文学名著里摘抄一些华丽的词藻,留着写作文用,她把爷爷的书翻来找去,一无所获:“爷爷写的什么呀,没词儿!”没想到汪曾祺却对“没词儿”这一评价十分满意。他在他自己的《小说笔谈》里说:“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所以他的文章,是人人都能读,人人都能懂的。那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淳朴、自在、通透与快乐,也能跟随着质朴的文字,在第一时间流淌进读者的心里。初翻《活着多好啊》这本书,看到目录时,恍然间还以为自己看的是一本菜谱:《手把肉》《萝卜》《干丝》《贴秋膘》……都说民以食为天,汪曾祺简直把这句话刻在了骨子里。他善于感受食物中的美好,再平凡的食物在他眼里都有自己独特之处。提及萝卜,他说“极脆嫩,有甜味,富水分……斜切为薄片,再切为细丝,加酱油、醋、香油略拌,撒一点青蒜,极开胃”。提及烤栗子,他说“丢几个栗子在通红的炭火里,一会儿,砰的一声,蹦出一个裂了壳的熟栗子,抓起来,在手里来回倒,连连吹气使冷,剥壳入口,香甜无比,是雪天的乐事”。寥寥几句,贴切又生动,透着一股子鲜活和亲切,看得人胃口大开。细细品来,这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也只有汪曾祺这样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有。吃饭是件乐事,对汪曾祺来说如此,对很多人来说应当也是如此。犹记得新冠疫情期间,我在社区设置的卡点处值守,进出往来的除了一线防控人员,就是要去超市采购生活必需品的群众了。因为封控,他们每户人家三天才能出门采购一次,有背着包的,有拎着框的,有拖着小拉车的,出门时都是行色匆匆,回来时人人收获满满。“诶,今天的白菜看起来好,多买点,娃儿喜欢吃。”“再买点面粉回去蒸包子吃。”我给他们做进出登记时也会闲聊几句,对答往往很可爱,带着对粮水充足的满足感,好像只要肚子能填饱了,暂时居家封控也不算什么事儿了,疫情的阴影也仿佛隔得远远的了,甚至有闲情逸致培养起自己的厨艺,闭关修炼几个月,在日后大显身手了。有天夜里,我值完班回到家,翻开《活着多好啊》,正看到汪曾祺在那特殊年代因政治原因被派到沽源县画马铃薯图谱,他那时的生活想必是很苦的,但他的文字里没有一丝苦痛,他形容这件事时说“想想也怪有意思”。他在墙角发现一株波斯菊,称它“竭力地放出浅紫浅紫的花来,为这座绝塞孤城增加了一分颜色,一点生气”。而他更多的笔墨用来描写沽源的美食:他品尝过的几十种不同样的马铃薯、终生难忘的羊肉口蘑臊子莜面、自己亲手采的蘑菇……看着看着,我不禁笑出声来: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会找点乐子,把每一个艰难的日子都过出花儿来,这么一颗朴素的热爱生活的心,不是汪曾祺独有的,而每一个如汪曾祺一般热爱生活的人,又是多么的鲜活可爱呀。“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若是一时被疲惫和艰辛遮蔽了双眼,那就翻开看看《活着真好啊》,在汪曾祺的文字里汲取热爱生活的力量打开发现生活的美的眼睛,看看这充满乐趣的人间,怀抱着对生活的热忱,继续朝着前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