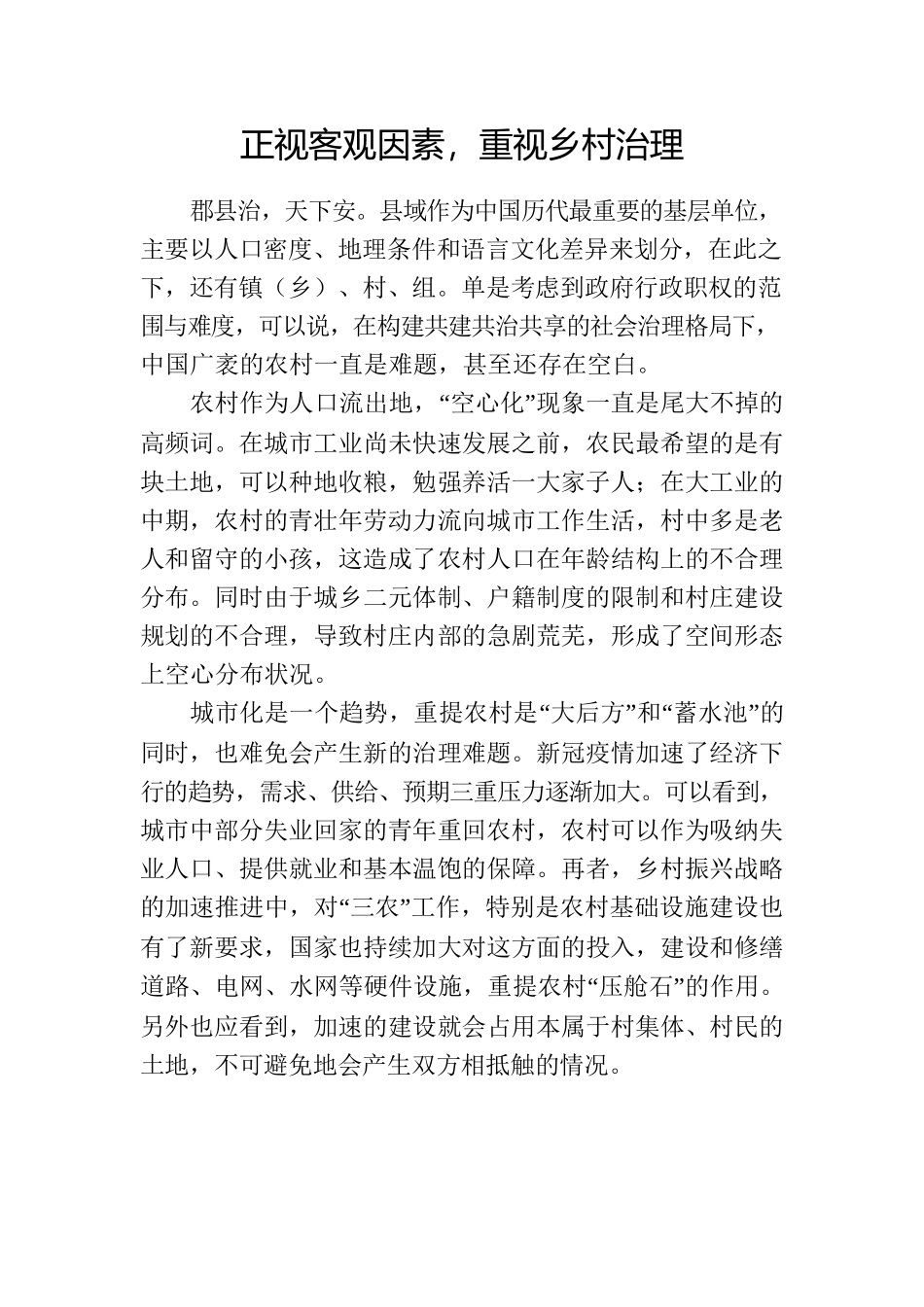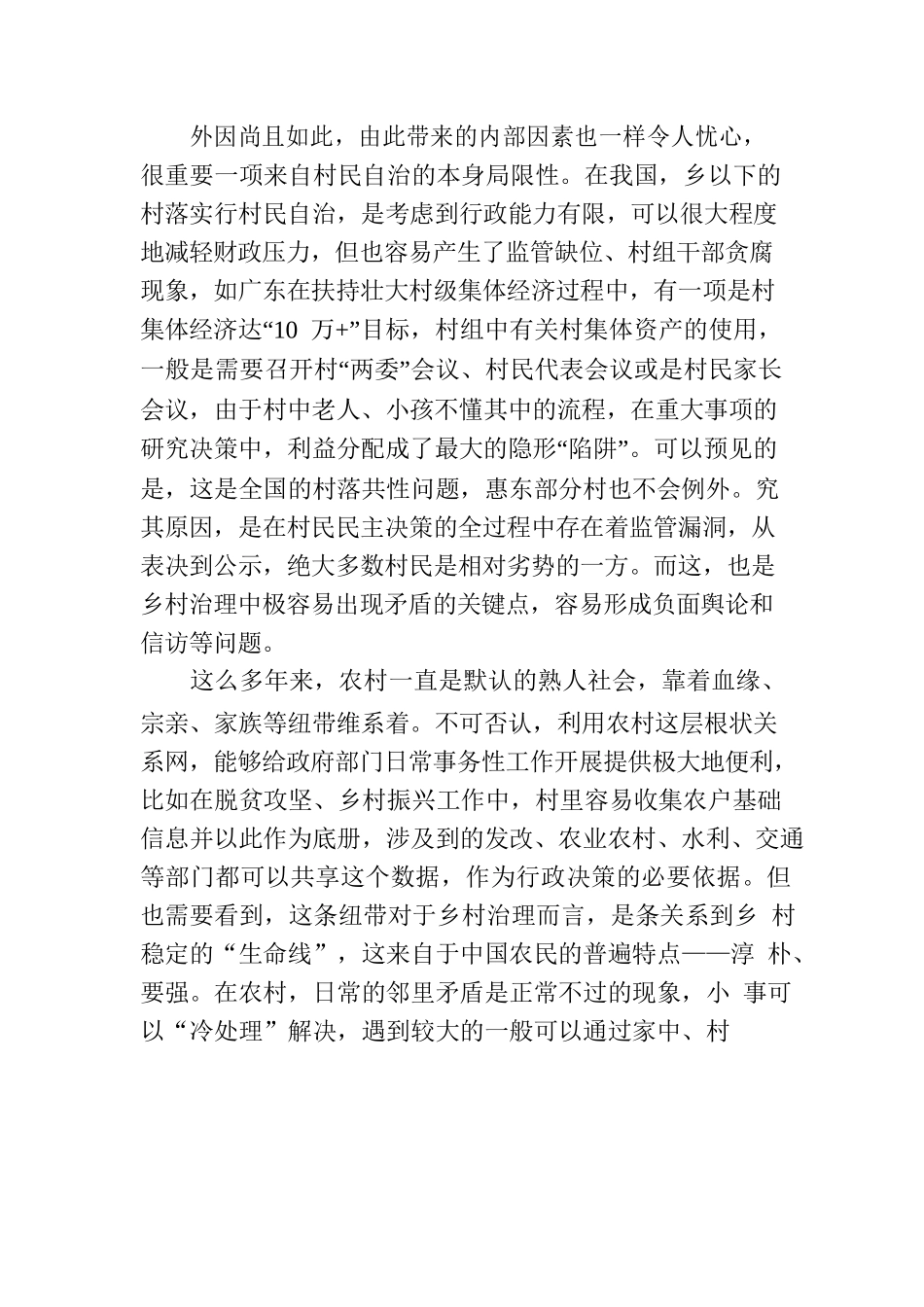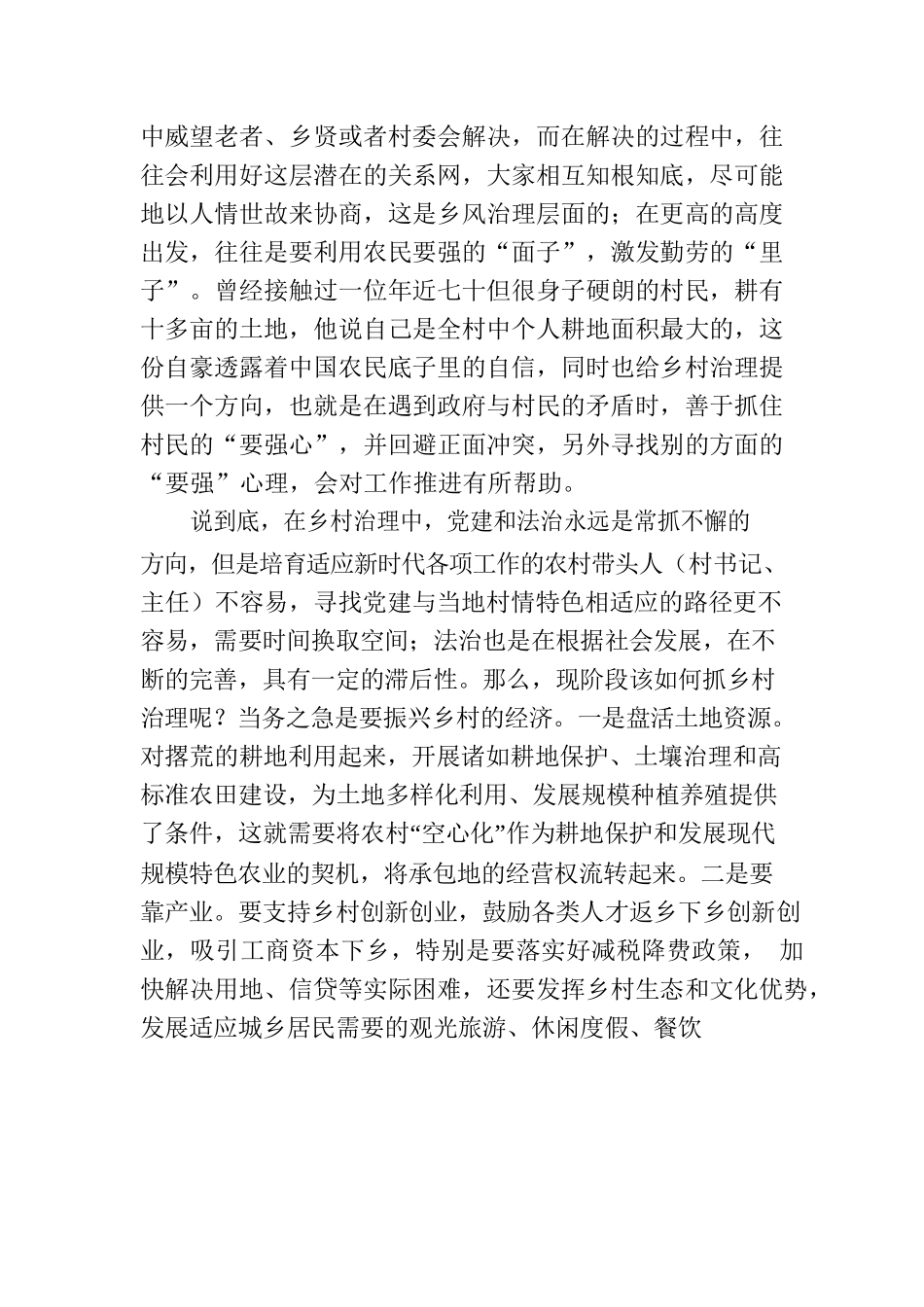正视客观因素,重视乡村治理郡县治,天下安。县域作为中国历代最重要的基层单位,主要以人口密度、地理条件和语言文化差异来划分,在此之下,还有镇(乡)、村、组。单是考虑到政府行政职权的范围与难度,可以说,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中国广袤的农村一直是难题,甚至还存在空白。农村作为人口流出地,“空心化”现象一直是尾大不掉的高频词。在城市工业尚未快速发展之前,农民最希望的是有块土地,可以种地收粮,勉强养活一大家子人;在大工业的中期,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作生活,村中多是老人和留守的小孩,这造成了农村人口在年龄结构上的不合理分布。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的限制和村庄建设规划的不合理,导致村庄内部的急剧荒芜,形成了空间形态上空心分布状况。城市化是一个趋势,重提农村是“大后方”和“蓄水池”的同时,也难免会产生新的治理难题。新冠疫情加速了经济下行的趋势,需求、供给、预期三重压力逐渐加大。可以看到,城市中部分失业回家的青年重回农村,农村可以作为吸纳失业人口、提供就业和基本温饱的保障。再者,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推进中,对“三农”工作,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了新要求,国家也持续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建设和修缮道路、电网、水网等硬件设施,重提农村“压舱石”的作用。另外也应看到,加速的建设就会占用本属于村集体、村民的土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双方相抵触的情况。外因尚且如此,由此带来的内部因素也一样令人忧心,很重要一项来自村民自治的本身局限性。在我国,乡以下的村落实行村民自治,是考虑到行政能力有限,可以很大程度地减轻财政压力,但也容易产生了监管缺位、村组干部贪腐现象,如广东在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过程中,有一项是村集体经济达“10万+”目标,村组中有关村集体资产的使用,一般是需要召开村“两委”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是村民家长会议,由于村中老人、小孩不懂其中的流程,在重大事项的研究决策中,利益分配成了最大的隐形“陷阱”。可以预见的是,这是全国的村落共性问题,惠东部分村也不会例外。究其原因,是在村民民主决策的全过程中存在着监管漏洞,从表决到公示,绝大多数村民是相对劣势的一方。而这,也是乡村治理中极容易出现矛盾的关键点,容易形成负面舆论和信访等问题。这么多年来,农村一直是默认的熟人社会,靠着血缘、宗亲、家族等纽带维系着。不可否认,利用农村这层根状关系网,能够给政府部门日常事务性工作开展提供极大地便利,比如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中,村里容易收集农户基础信息并以此作为底册,涉及到的发改、农业农村、水利、交通等部门都可以共享这个数据,作为行政决策的必要依据。但也需要看到,这条纽带对于乡村治理而言,是条关系到乡村稳定的“生命线”,这来自于中国农民的普遍特点——淳朴、要强。在农村,日常的邻里矛盾是正常不过的现象,小事可以“冷处理”解决,遇到较大的一般可以通过家中、村中威望老者、乡贤或者村委会解决,而在解决的过程中,往往会利用好这层潜在的关系网,大家相互知根知底,尽可能地以人情世故来协商,这是乡风治理层面的;在更高的高度出发,往往是要利用农民要强的“面子”,激发勤劳的“里子”。曾经接触过一位年近七十但很身子硬朗的村民,耕有十多亩的土地,他说自己是全村中个人耕地面积最大的,这份自豪透露着中国农民底子里的自信,同时也给乡村治理提供一个方向,也就是在遇到政府与村民的矛盾时,善于抓住村民的“要强心”,并回避正面冲突,另外寻找别的方面的“要强”心理,会对工作推进有所帮助。说到底,在乡村治理中,党建和法治永远是常抓不懈的方向,但是培育适应新时代各项工作的农村带头人(村书记、主任)不容易,寻找党建与当地村情特色相适应的路径更不容易,需要时间换取空间;法治也是在根据社会发展,在不断的完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那么,现阶段该如何抓乡村治理呢?当务之急是要振兴乡村的经济。一是盘活土地资源。对撂荒的耕地利用起来,开展诸如耕地保护、土壤治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土地多样化利用、发展规模种植养殖提供了条件,这就需要将农村“空心化”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