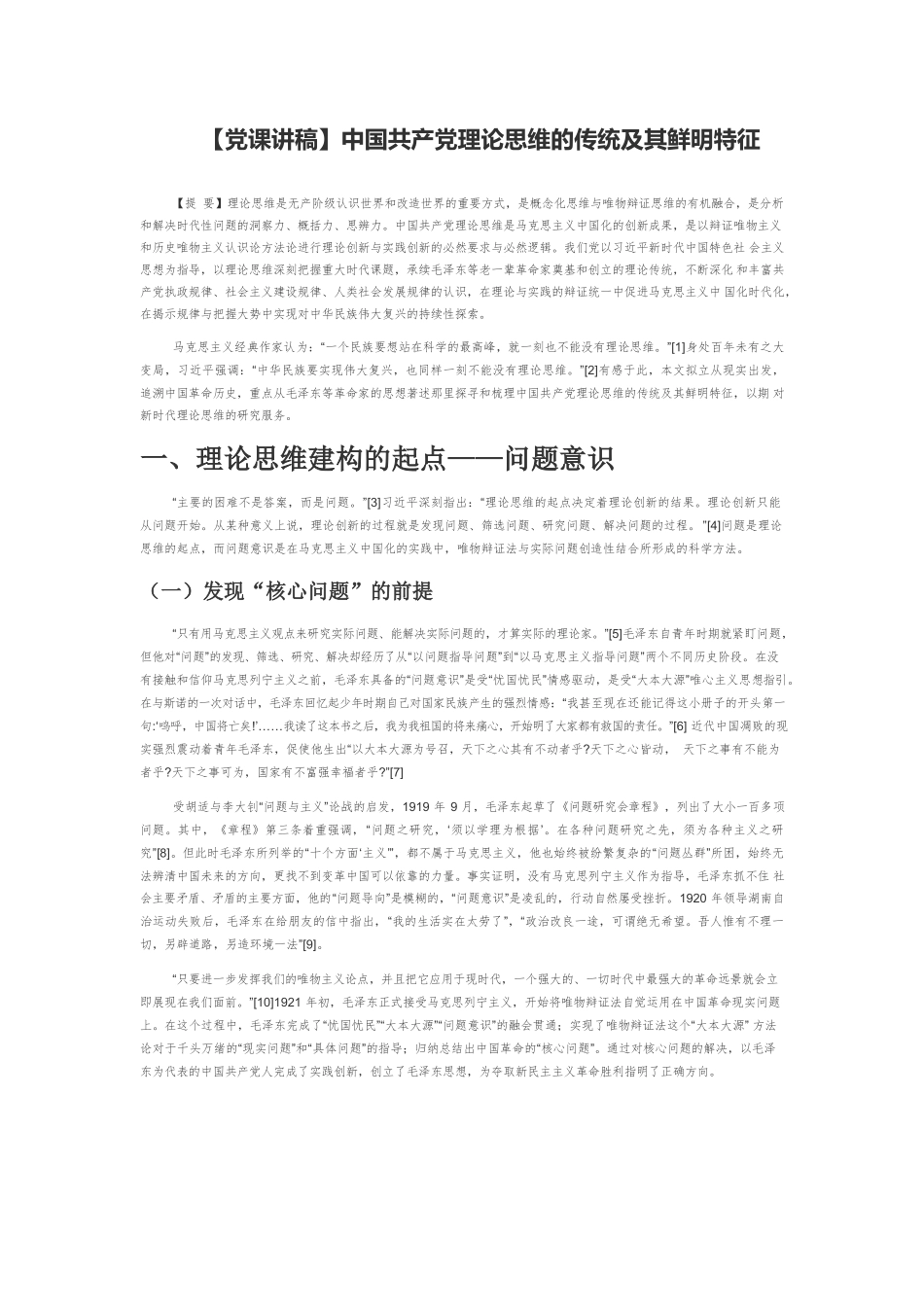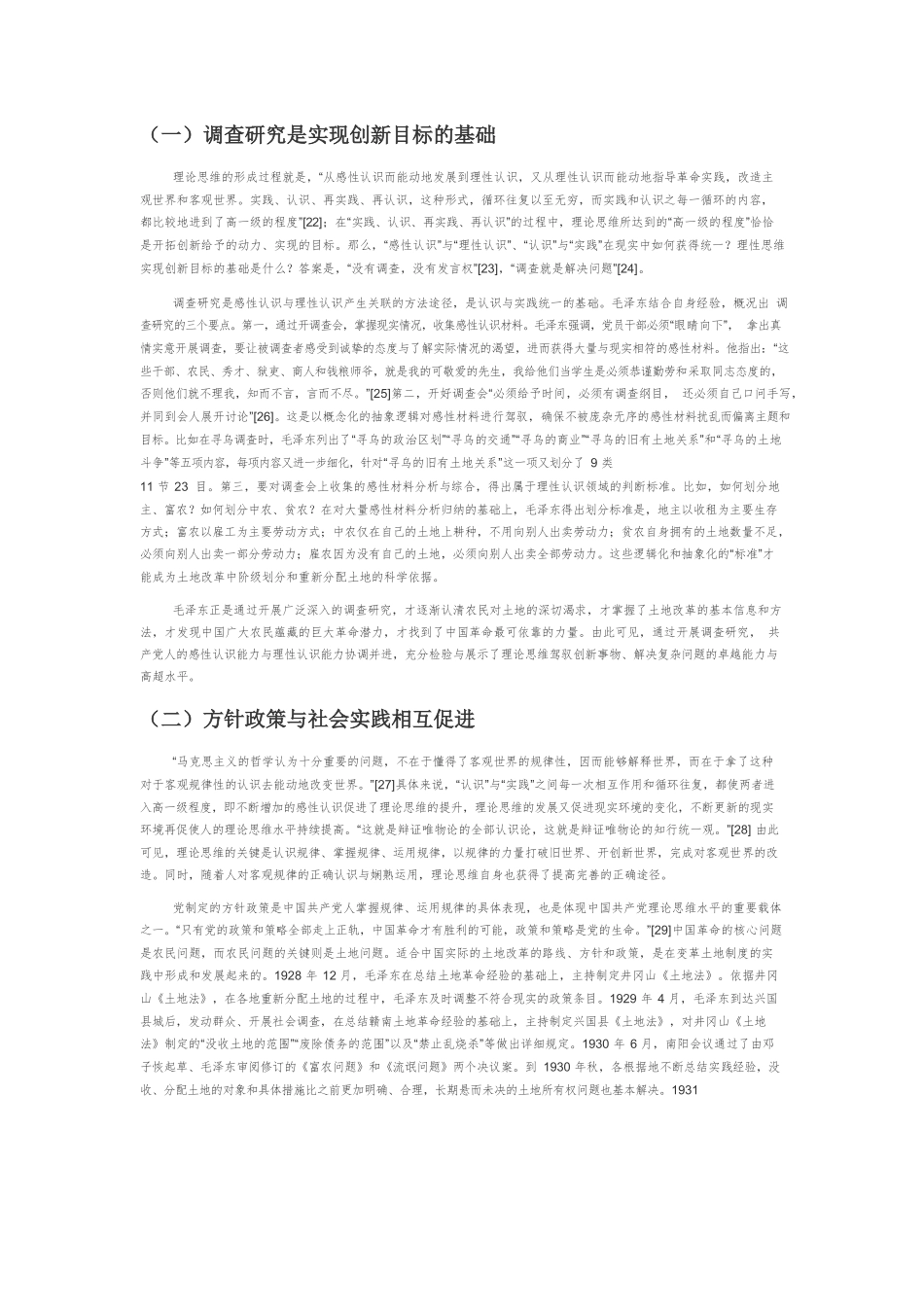【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理论思维的传统及其鲜明特征【提要】理论思维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式,是概念化思维与唯物辩证思维的有机融合,是分析和解决时代性问题的洞察力、概括力、思辨力。中国共产党理论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进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必然要求与必然逻辑。我们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理论思维深刻把握重大时代课题,承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奠基和创立的理论传统,不断深化和丰富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揭示规律与把握大势中实现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持续性探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有感于此,本文拟立从现实出发,追溯中国革命历史,重点从毛泽东等革命家的思想著述那里探寻和梳理中国共产党理论思维的传统及其鲜明特征,以期对新时代理论思维的研究服务。一、理论思维建构的起点——问题意识“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3]习近平深刻指出:“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4]问题是理论思维的起点,而问题意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唯物辩证法与实际问题创造性结合所形成的科学方法。(一)发现“核心问题”的前提“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5]毛泽东自青年时期就紧盯问题,但他对“问题”的发现、筛选、研究、解决却经历了从“以问题指导问题”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在没有接触和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毛泽东具备的“问题意识”是受“忧国忧民”情感驱动,是受“大本大源”唯心主义思想指引。在与斯诺的一次对话中,毛泽东回忆起少年时期自己对国家民族产生的强烈情感:“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6]近代中国凋败的现实强烈震动着青年毛泽东,促使他生出“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7]受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启发,1919年9月,毛泽东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列出了大小一百多项问题。其中,《章程》第三条着重强调,“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8]。但此时毛泽东所列举的“十个方面‘主义’”,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他也始终被纷繁复杂的“问题丛群”所困,始终无法辨清中国未来的方向,更找不到变革中国可以依靠的力量。事实证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毛泽东抓不住社会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他的“问题导向”是模糊的,“问题意识”是凌乱的,行动自然屡受挫折。1920年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在给朋友的信中指出,“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9]。“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10]1921年初,毛泽东正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将唯物辩证法自觉运用在中国革命现实问题上。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完成了“忧国忧民”“大本大源”“问题意识”的融会贯通;实现了唯物辩证法这个“大本大源”方法论对于千头万绪的“现实问题”和“具体问题”的指导;归纳总结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通过对核心问题的解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实践创新,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二)筛选、研究“核心问题”的途径“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