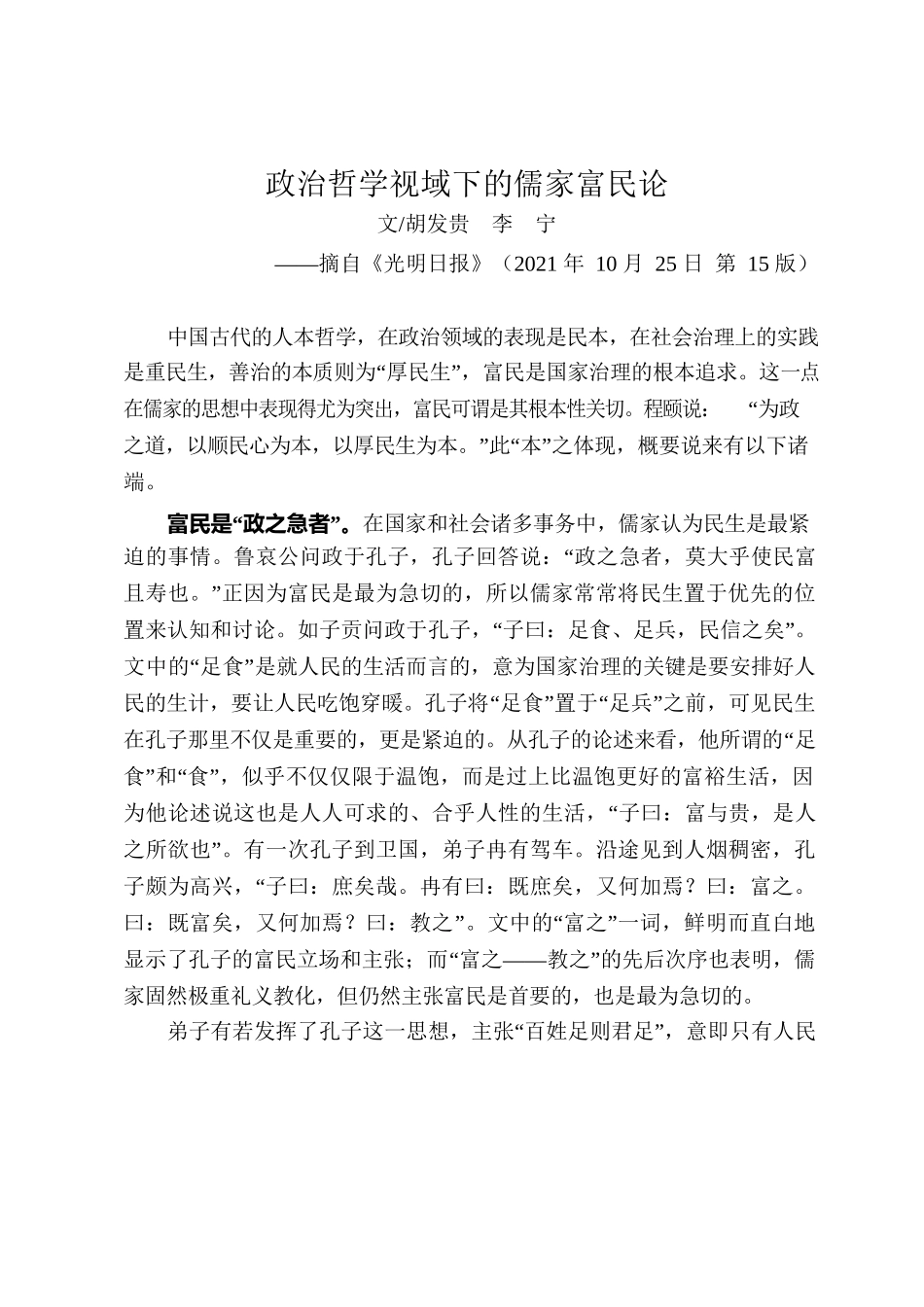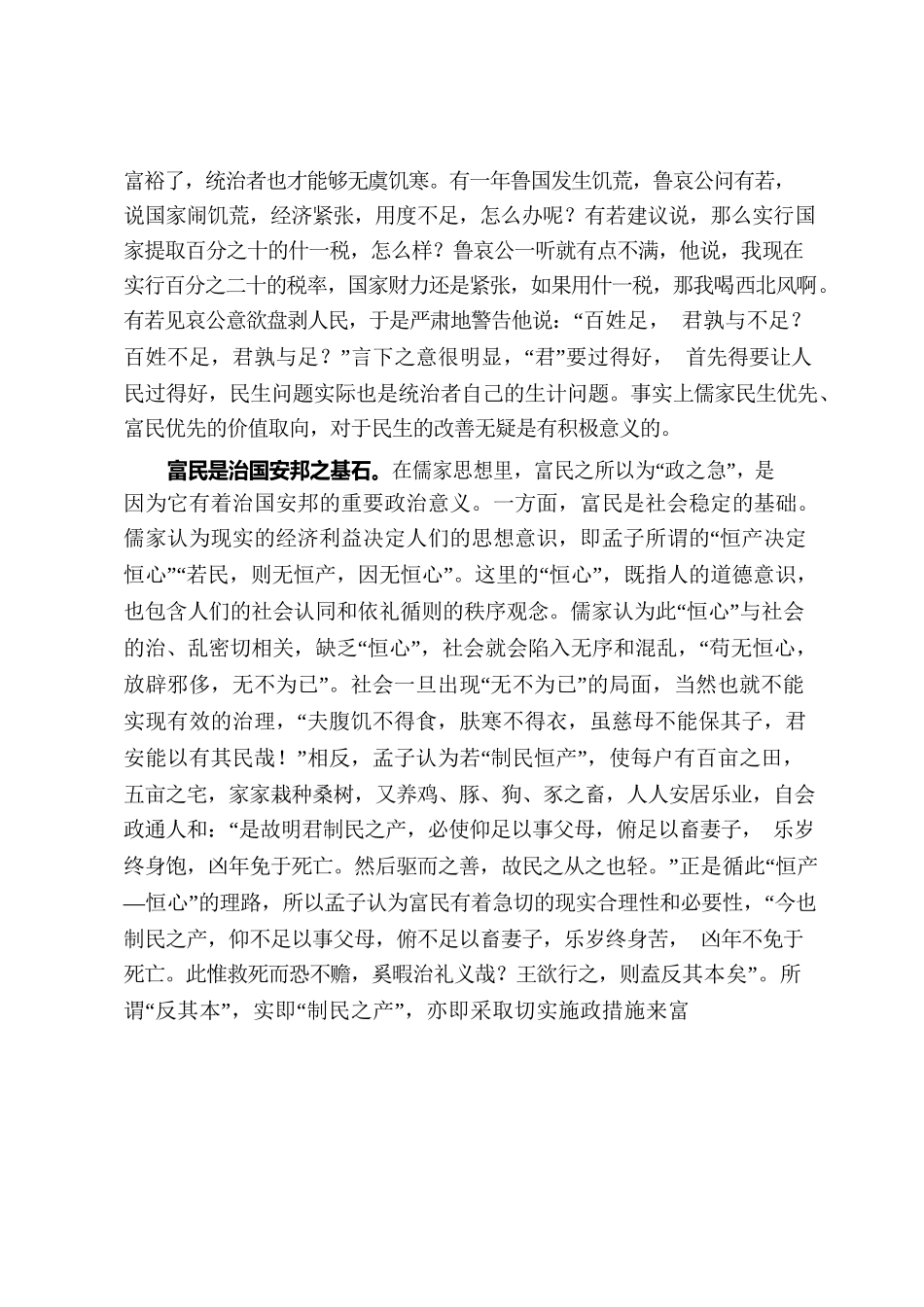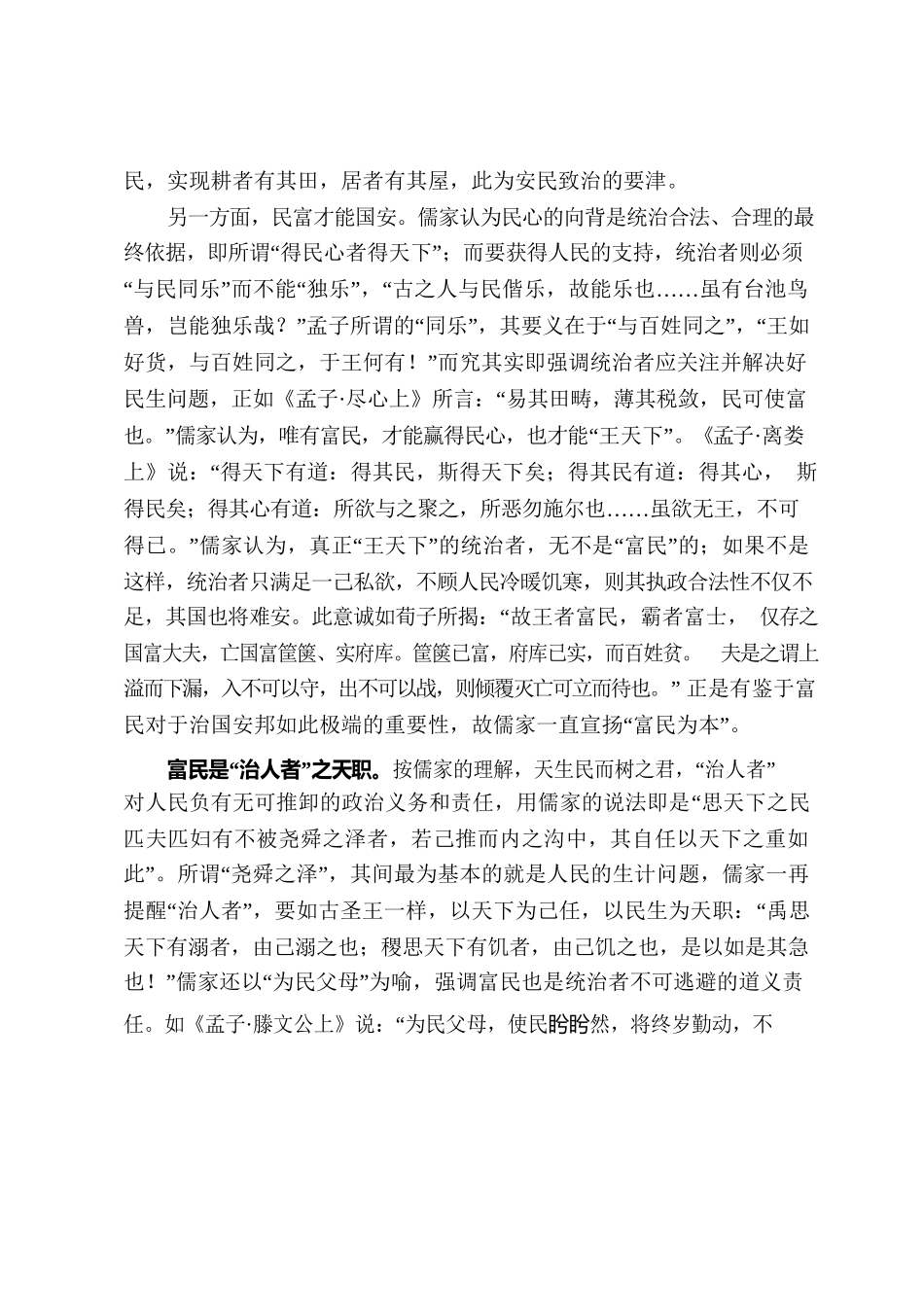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儒家富民论文/胡发贵李宁——摘自《光明日报》(2021年10月25日第15版)中国古代的人本哲学,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是民本,在社会治理上的实践是重民生,善治的本质则为“厚民生”,富民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追求。这一点在儒家的思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富民可谓是其根本性关切。程颐说:“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此“本”之体现,概要说来有以下诸端。富民是“政之急者”。在国家和社会诸多事务中,儒家认为民生是最紧迫的事情。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正因为富民是最为急切的,所以儒家常常将民生置于优先的位置来认知和讨论。如子贡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文中的“足食”是就人民的生活而言的,意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计,要让人民吃饱穿暖。孔子将“足食”置于“足兵”之前,可见民生在孔子那里不仅是重要的,更是紧迫的。从孔子的论述来看,他所谓的“足食”和“食”,似乎不仅仅限于温饱,而是过上比温饱更好的富裕生活,因为他论述说这也是人人可求的、合乎人性的生活,“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弟子冉有驾车。沿途见到人烟稠密,孔子颇为高兴,“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文中的“富之”一词,鲜明而直白地显示了孔子的富民立场和主张;而“富之——教之”的先后次序也表明,儒家固然极重礼义教化,但仍然主张富民是首要的,也是最为急切的。弟子有若发挥了孔子这一思想,主张“百姓足则君足”,意即只有人民富裕了,统治者也才能够无虞饥寒。有一年鲁国发生饥荒,鲁哀公问有若,说国家闹饥荒,经济紧张,用度不足,怎么办呢?有若建议说,那么实行国家提取百分之十的什一税,怎么样?鲁哀公一听就有点不满,他说,我现在实行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国家财力还是紧张,如果用什一税,那我喝西北风啊。有若见哀公意欲盘剥人民,于是严肃地警告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言下之意很明显,“君”要过得好,首先得要让人民过得好,民生问题实际也是统治者自己的生计问题。事实上儒家民生优先、富民优先的价值取向,对于民生的改善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富民是治国安邦之基石。在儒家思想里,富民之所以为“政之急”,是因为它有着治国安邦的重要政治意义。一方面,富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儒家认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即孟子所谓的“恒产决定恒心”“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这里的“恒心”,既指人的道德意识,也包含人们的社会认同和依礼循则的秩序观念。儒家认为此“恒心”与社会的治、乱密切相关,缺乏“恒心”,社会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社会一旦出现“无不为已”的局面,当然也就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相反,孟子认为若“制民恒产”,使每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家家栽种桑树,又养鸡、豚、狗、豕之畜,人人安居乐业,自会政通人和:“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正是循此“恒产—恒心”的理路,所以孟子认为富民有着急切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所谓“反其本”,实即“制民之产”,亦即采取切实施政措施来富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此为安民致治的要津。另一方面,民富才能国安。儒家认为民心的向背是统治合法、合理的最终依据,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获得人民的支持,统治者则必须“与民同乐”而不能“独乐”,“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所谓的“同乐”,其要义在于“与百姓同之”,“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而究其实即强调统治者应关注并解决好民生问题,正如《孟子·尽心上》所言:“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