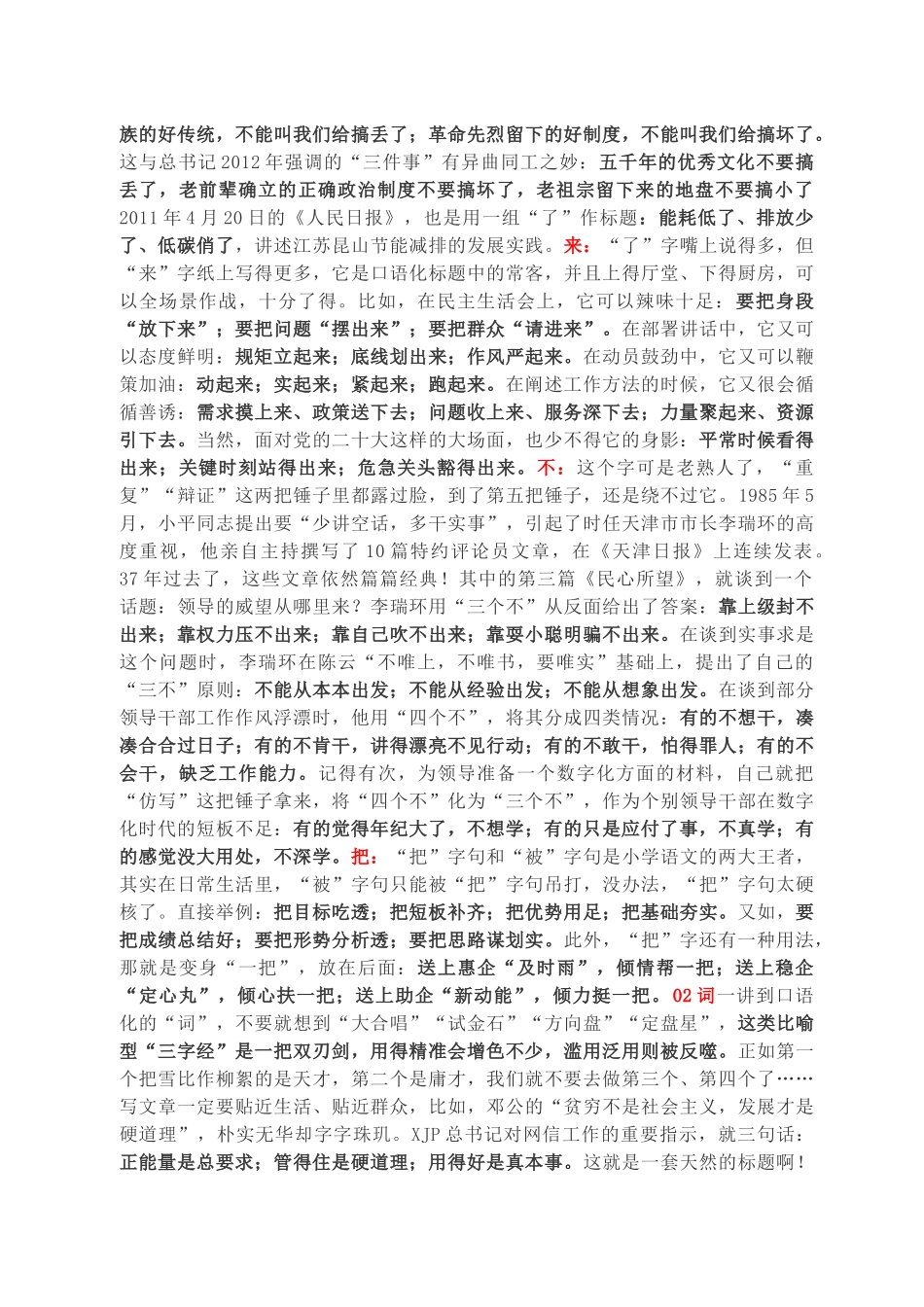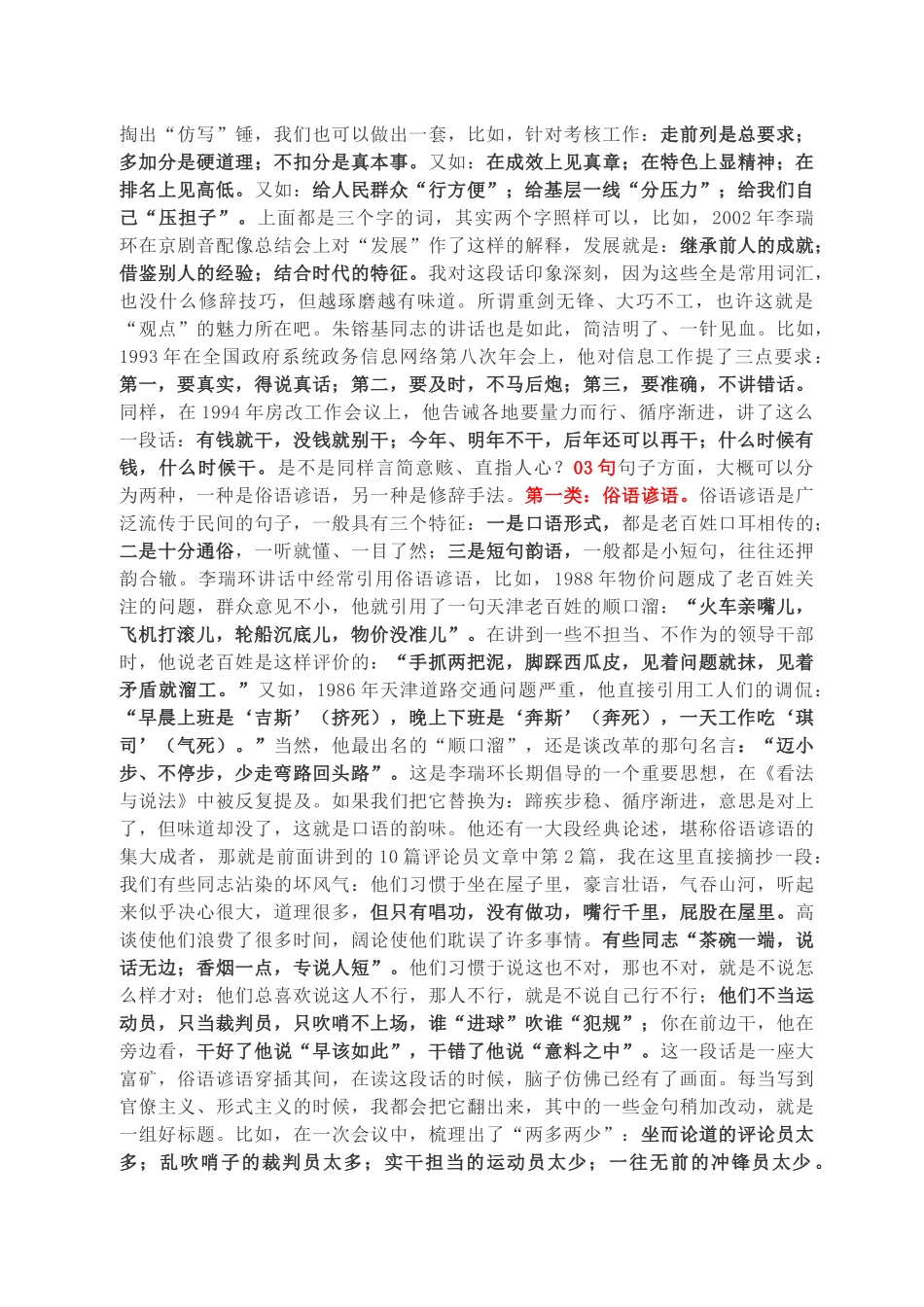今天,我们来讲讲第5把“符号锤”——口语的韵味。这个韵味来自哪里?我觉得可以从以下3方面来看:第一,这个韵味来自于“声音”。语言的第一属性是什么?不是文字,而是声音,这就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所强调的:口语处于首要地位!是先有口语,还是先有文字?肯定是先有口语。人类历史上有数以万计的语言,只有106种语言使用过文字或产生了文学。现存的3000种语言中,大约只有78种语言有书面文献。交流的本质是“声音”,就算你在阅读文字的时候,脑子里也会不自觉响起一种声音。不信的话,现在就可以试一试。所以,语言首先是一种口语现象,“口语”在一切交流中都处于首要地位。第二,这个韵味来自于“传播”。从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来看,概念最大的是语言,然后是文字,文字下面又包含口语文字、书面文字。但归根结底它们的根本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传播”,凡是与这个中心目的相违背的,都是耍流氓。讲一个“秀才买柴”的故事。一个秀才看到一个挑担卖柴的,喊道:“荷薪者过来。”卖柴人听懂了“过来”两字,就过来了。秀才指着柴问:“其价几何?”卖柴人听懂了一个字:“价”,就告诉他了。秀才又摇头晃脑地说:“其薪枝多而茎少,烟多而焰少,请损之!”意思是:你这个柴小枝多、大段少,烟多、火不旺,便宜点吧。卖柴人一个字也没听懂,扭头走了。秀才的话有没有文化?有!但有没有用?没有!这就是我们在文稿写作中经常犯的“书生病”“拽文病”。你老老实实说“人话”就行了,非得故作高深,别人听得难受,没有传播效果,一切都是白费。书面语的传播力低于口语,这不是什么原理问题,这是生理问题。第三,这个韵味来自于“互动”。口语毕竟是琐碎的、不成体系的,经过人们的不断加工、提纯,最后转化为书面语,我们得到了书面语的精准,但也使得它与口语之间产生了距离。每一个文字,在诞生之初都是伴随着语境的,这就是口语的另外一大优势:可共情、能互动。比如,1983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现代化建设,讲了著名的“八字”方针: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正是这两句大白话,把保民生与抓发展之间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如果把“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句大白话翻译成书面语,应该就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同样是八个字,但我们会发现,很明显前者更有温度,因为它来自日常生活,有烟火气。好了,以上是道理的“心法”,下面我们谈谈实践的“技法”。这个技法不太好写,因为“口语”这把符号锤特点就像口语一样,虽然天天嘴巴上讲,但真要总结,好像又没什么特点。这个时候只能再次翻开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整整四册、64万字,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从嘴巴里讲出来的。所以,我准备以这本书为主,同时兼顾其他素材,尝试着去摸一摸“口语”这把锤子的门道。从文本形式上,我将其分为“字”“词”“句”三大类:01字所谓“字”,就是口语化标题出现频次较高的字,主要有这么一些:了:我们每个人讲得最多的一个字,也许就是“了”,作为一个语气助词,它天生就有口语基因。1985年1月,李瑞环同《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的记者谈话,他用“十个了”,讲述了天津发展之变:天变青了;地变绿;房变多了;路变宽了;水变甜了;害变利了;脏变净了;破变好了;难变易了;城变美了。1994年2月,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筹备领导小组会上,他用“三个了”阐明了什么是大是大非:祖宗留下这块地皮,不能叫我们给搞小了;中华民族的好传统,不能叫我们给搞丢了;革命先烈留下的好制度,不能叫我们给搞坏了。这与总书记2012年强调的“三件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不要搞丢了,老前辈确立的正确政治制度不要搞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地盘不要搞小了2011年4月20日的《人民日报》,也是用一组“了”作标题:能耗低了、排放少了、低碳俏了,讲述江苏昆山节能减排的发展实践。来:“了”字嘴上说得多,但“来”字纸上写得更多,它是口语化标题中的常客,并且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可以全场景作战,十分了得。比如,在民主生活会上,它可以辣味十足:要把身段“放下来”;要把问题“摆出来”;要把群众“请进来”。在部署讲话中,它又可以态度鲜明:规矩立起来;底线划...